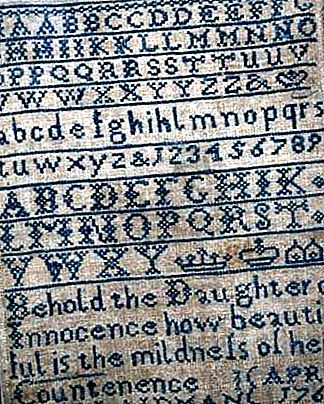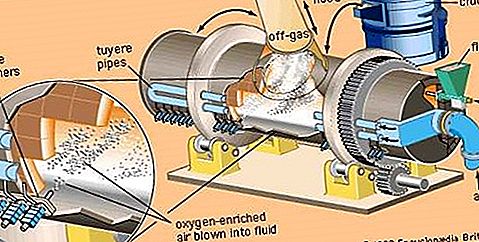爱国主义,对一个国家,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依恋和承诺的感觉。爱国主义(对国家的爱)和民族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忠诚)通常被视为同义词,但是爱国主义起源于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大约2,000年前。

希腊特别是罗马的上古为政治爱国主义提供了根源,这种政治爱国主义将对爱国者的忠诚视为对共和国政治概念的忠诚。它与对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热爱,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以及对一个国家公正行事的责任相关。爱国主义的古典罗马含义在15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背景下重新出现。在这里,爱国主义代表着城市的共同自由,只有公民的公民精神才能维护这一自由。对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而言,对共同自由的热爱使公民能够将自己的私人利益和特殊利益视为共同利益的一部分,并帮助他们抵制腐败和暴政。虽然对城市的热爱通常会因其军事实力和文化优势而感到自豪,但正是城市的政治机构和生活方式构成了这种爱国主义依恋的独特焦点。热爱城市就是为了保护共同自由而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包括生命)。
与经典的共和主义爱国主义观念相反,让·雅克·卢梭的《波兰政府思考》可以看作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联系的早期实例。卢梭倡导热爱民族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他认为民族文化之所以有价值,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培养对政治祖国的忠诚。因此,卢梭的民族主义源于并典型地表现出共和党人对确保公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忠诚的共和主义。
在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更明确的联系。在赫德看来,爱国主义不是指政治美德,而是指对国家的精神依附。在这种情况下,祖国成为国家及其独特语言和文化的代名词,这赋予了国家统一与连贯性。因此,赫德没有将爱国主义与维护政治自由联系起来,而是将对一个国家的热爱与维护共同文化和人民的精神统一联系在一起。在古典的共和党传统中,“祖国”是政治机构的代名词,对牧民而言,民族是前政治的,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使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独特性。因此,爱国主义与对自身文化的排他性依恋联系在一起,因此反对世界主义和文化同化。自由不等于与反对政治压迫的斗争,而是等于保留一个独特的人民和爱国牺牲,以确保国家的长期生存。
爱国主义与对一个国家的专属依恋之间的这种联系使批评家们认为爱国自豪感在道德上是危险的,从而产生了沙文主义,不符合国际化的抱负,并承认所有人的平等道德价值。对爱国主义采取了更多具有同情心的方法,以新的忠诚形式为基础,这种忠诚与普遍价值观念,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对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容忍相适应。对爱国主义重新产生兴趣的核心是相信,要保持稳定,民主社会就必须对其公民有强烈的忠诚感。代表当代社会的高度多元化不仅可能引起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分歧,可能破坏政体的稳定,而且致力于一定程度平等的现代民主国家依赖于公民为共同利益做出牺牲的意愿,无论是根据收入的日常再分配来满足福利需求还是提供集体商品和服务,例如教育或医疗保健。因此,在倡导新形式爱国主义的人眼中,稳定的民主社会需要强烈的团结感。
寻求新的团结形式的最突出例子是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宪法爱国主义)概念,其目的是建立公民的忠诚,而不是建立在政治上的,同质的社区中,而是致力于实现普遍的自由主义。现代自由国家宪法所载的原则。为了确保订阅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生活方式的公民能够平等地在本国共存并与自己的国家认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宪法国家必须确保其政治文化不偏爱或歧视任何国家。特定的亚文化。为此,至关重要的是将多数文化与基于基本宪法原则和基本法的共同政治文化区分开。因此,一个公民国家的会员资格不再取决于对共同语言或共同的伦理和文化渊源的呼吁,而仅反映了基于标准自由宪法原则的共同政治文化。哈贝马斯试图将爱国主义作为对普遍自由主义原则的依附的尝试,也与有时被称为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有关,后者试图在承认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基础上建立后国家的认同,人权和人权是在特定宪法传统中概念化的。
英国出生的美国哲学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等倡导者说,这种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这种主义将对一个国家的依恋和文化特殊性相结合,对不同地方和不同民族的欣赏以及对平等道德的强烈尊重所有人类的价值。宪法爱国主义形式的拥护者经常以美国为例,以明确的政治爱国主义将非国家政体团结在一起。例如,美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沙尔(John Schaar)将美国爱国主义称为“盟约爱国主义”,这是一种爱国依恋的形式,其特征在于对创始盟约所确立的原则和目标的承诺以及履行创始联盟工作的义务父亲 当代的另一种思想诉诸于共和主义的古典共和主义原则,即对自由的热爱,积极的公民权和自我牺牲,以谋求共同利益,以试图形成新的团结形式,而这种团结形式不依赖于政治前,种族同质的国家的思想。 。
但是,对于这种试图产生新的,非排他性的团结形式的批评家,对爱国主义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对普遍原则的承诺相一致表示怀疑。尽管对宪法爱国主义的批评者对哈贝马斯试图将政治文化与更广泛的多数文化脱钩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但他指出,像美国这样具有多元文化的社会,政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饱含民族色彩的象征和神话。具有政治前意义,英国哲学家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等评论家认为,古典共和党的爱国主义比共和党传统的现代拥护者更为自由和对外界的敌视。根据卡诺万(Canovan)的观点,不仅古典共和党传统中庆祝的爱国美德主要是军事美德,而且共和党人对公民的教育和社会化的重视,以系统地灌输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国家的承诺,许多当代自由主义者很容易将其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操纵和灌输形式。此外,立宪和现代共和主义爱国主义的拥护者通常以存在既定的政治边界和共同的政治体制为前提,这些政治边界和共同的政治体制起源于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巩固。因此,在爱国主义与普遍价值观,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对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容忍的承诺之间可以调和的程度仍然存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