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印第安语言,是美国和加拿大本土的语言,在墨西哥边境以北使用。但是,该地区的许多语言群体都延伸到墨西哥,有些甚至远至中美洲。本文重点介绍加拿大,格陵兰和美国的母语。(有关墨西哥和中美洲本国语言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中美洲印第安语。另请参见爱斯基摩语-阿留特语。)
北美印第安语言多种多样。首次与欧洲接触时,有300多种。根据《濒危语言目录》(endangeredlanguages.com),在21世纪初期,北美仍使用150种土著语言,美国仍使用112种土著语言,加拿大使用60种土著语言。 (有22种语言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发言者)。在这大约200种语言中,有123种不再以母语为母语(即以该舌头为母语的语言),并且许多语言少于10种。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威胁。这些语言的丰富多样性为语言学提供了宝贵的实验室。当然,如果没有对美洲原住民语言研究的贡献,语言学学科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发展,尤其是在美国。在本文中,当前时态将用于指代已存在和尚存的语言。
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是如此多样,以至于没有所有人共享的功能或复杂的功能。同时,这些语言没有原始的东西。它们使用的语言资源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语言一样,具有相同的规律性和复杂性。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被分为57个语言族,包括14个较大的语言族,18个较小的语言族和25个孤立语(没有已知亲戚的语言,因此只有一个成员语言的语言族)。在地理上,某些地区的多样性也很明显。落基山脉以西有37个家庭,其中20个仅存在于加利福尼亚州。因此,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显示出比整个欧洲更多的语言多样性。
这些语言家族彼此独立,并且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为止,没有一个可以证明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许多提案试图将其中一些加入到由声称彼此之间亲近的家庭组成的更大的群体中。这些提议中的一些似乎是合理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尽管其中有一些完全是猜测。有可能,也许是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彼此联系,但是它们很久以前彼此分离,并且在这段时间里变化很大,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任何关系。一个主要的问题与在较深的历史水平上难以区分由于共同祖先的继承和语言借用的继承而共享的相似之间有困难。
在任何情况下,北美印第安语言的共同起源理论都没有认真的追随者。大多数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北美最初是由从亚洲穿越白令海峡移民的人居住的。已经尝试将美洲原住民语言与亚洲语言联系起来,但是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确,北美土著人的语言多样性实际上表明,该地区的人口稠密是由于至少三波,可能是几波不同的亚洲移民潮。但是,他们带来的语言在亚洲没有可辨认的亲戚。
分类
美国人约翰·卫斯理·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于1891年对北美印第安语言家族进行了首次全面分类,他的研究基于词汇的印象派相似性。鲍威尔确定了58个语言家族(称为“股票”)。鲍威尔(Powell)所采用的命名原则从那以后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Caddoan是包括Caddo和其他相关语言的家族的名称。鲍威尔的分类仍然适用于他所识别的更明显的家族,尽管自从他的时代以来,鲍威尔的分类已经取得了许多发现和进步,因此现在鲍威尔的一些分组已经合并在一起,并且增加了新的分组。
各种各样的学者试图将这些家庭分成更大的单元,以反映更深层次的历史关系。在这些努力中,最雄心勃勃且最著名的是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的著作,该书于1929年在《百科全书》上发表。在萨皮尔的分类中,所有语言都分为六种门-爱斯基摩人-阿留特,阿尔贡奎安-(Algonkian -)Wakashan,Na-Dené,Penutian,Hokan-Siouan和Aztec-Tanoan –基于非常普遍的语法相似之处。
还进行了许多其他尝试,以将美洲印第安人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减少为由较少的独立语言族组成的更易于管理的方案,但是大多数方案都没有证明是成功的。在这些尝试中,最著名的也许是1987年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H. Greenberg)提出的假说,该假说试图将美洲的大约180种独立语言家族(包括孤立家族)归为一个大家族,他称之为“ Amerind”-它把除Eskimo-Aleut和Na-Dené之外的所有美国语言族聚在一起。该提议所基于的方法已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并且所引用的数据被证明是有缺陷的。现在,该假设已被语言学家所抛弃。
在21世纪初期,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瓦杰达(Edward Vajda)提出了在北美的Na-Dené(Athabaskan-Eyak-Tlingit)与西伯利亚中部的Yeniseian语言家族之间建立亲属关系的提议。尽管起初很吸引人,但是带有推定声音对应关系的词汇证据或为其所引证的语法(形态)证据都不足以支持这种提议的关系。
语言联系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北美许多土著语言之间也存在语言接触。这些语言显示出与其他语言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语言之间不仅可以借用词汇,还可以借用语音,语法和其他功能。在许多定义明确的语言领域中,各族的语言通过借阅过程而具有许多结构特征。在北美,最著名的是西北海岸语言区,尽管还有其他几个。在少数情况下,语言接触的情况引起了皮金斯语或贸易语言。在北美最著名的是在西北美洲印第安人团体中广泛使用的奇努克·贾贡(Chinook Jargon),以及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和墨西哥湾沿岸的部落中广泛使用的美孚力雅·贾贡。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混合语言发展起来,并与新的种族群体如何认同自己有关。Michif(加拿大法语和Cree贸易语言)的讲者在种族上自称Métis,是讲法语的毛皮商人和Cree妇女的后裔。在大多数名词和形容词(及其发音和语法)为法语的情况下,Michif则是混合的,而动词为Plains Cree(包括其发音和语法)的情况。Mednyj Aleut(铜岛Aleut)起源于定居在铜岛上的阿留申族和俄罗斯海豹猎人的混合种群。Mednyj Aleut的大部分词汇都是Aleut,但动词的语法大多是俄语。
平原手语用于部落间的交流。Kiowa以出色的手语演讲者而闻名。平原乌鸦被认为可以向他人传播手语。手语成为平原的通用语言,并传播到艾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
美洲印第安人团体与欧洲人之间的接触导致词汇量的借用,有些团体很少从欧洲人那里借钱,而其他团体则更多。欧洲语言也从美洲原住民语言中借用了术语。根据社会文化因素,美洲印第安人群体对欧洲文化的语言适应类型和程度差异很大。例如,在西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卡鲁克人(Karuk)中,一个遭受白人对待的部落遭到了严厉的对待,只有少数借来的单词来自英语,例如“阿普斯”(apple)和“ calques”(借贷翻译),例如“梨”被称为vírusur“熊”,因为在Karuk中p和b的声音与英语中的梨和熊的声音没有区别。大量的关于新的适应项目的词语是基于本地词语生成的,例如,一家旅馆被称为amnaam“就餐场所”。美国原住民语言从荷兰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称为西班牙裔)和瑞典语中借用了单词。
美洲印第安人语言为欧洲语言贡献了许多单词,尤其是植物,动物和本土文化物品的名称。在阿尔冈琴语中,英语有北美驯鹿,花栗鼠,山核桃,人类,莫卡辛,驼鹿,麦草,负鼠,木瓜,pemmican,柿子,powwow,浣熊,sachem,臭鼬,南瓜,南瓜,雪橇,战斧,图腾,wick其他; 来自chuckawalla(蜥蜴)的Cahuilla;来自Chinook Jargon,cayuse(最终是欧洲人),muck-a-muck,potlatch等。来自鲍鱼科斯塔诺安;来自蒂皮(帐篷)达科他州;来自爱斯基摩人,圆顶冰屋,皮艇,穆克卢克;来自霍根州纳瓦霍人;来自Salishan,coho(鲑鱼),ssquatch,sockeye(鲑鱼);和别的。
许多地名也源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一些例子是:密西西比州(奥吉布瓦的“大” +“河”);阿拉斯加(Aleut'将海面撞向');康涅狄格(Mohegan'长河'); 明尼苏达州(Dakota mnisota'多云的水');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Platte River),尼布达卡(Nibdhathka)“平河”);和田纳西州(Cherokee tanasi,小田纳西河的名字)。俄克拉荷马州由乔克托州州长艾伦·赖特(Allen Wright)代替俄克拉荷马州(Choctaw okla)的“人,部落,民族”和霍马“红色”创造。
语法
这里使用的术语“语法结构”既指形态学的传统类别(组成单词的语法片段)又指句法(如何将单词组合成句子)。应该再次强调的是,在语法以及语音或语义结构中,美洲印第安人语言和世界上任何其他语言都没有显示出任何可能被称为“原始”的东西。每种语言都像拉丁语,英语或任何欧洲语言一样复杂,微妙并且能满足所有交流需求。
(在下面的示例中,从语音字母中采用了拉丁字母中未找到的符号。)北美印第安语言在语法上显示出极大的多样性,因此不存在其存在与否将其表征为语法特征的语法特性。组。同时,有些特征虽然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为人所知,并且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语言中都没有发现,但是它们已经足够广泛地与美洲的语言相关联。在许多北美印第安语言家族中发现的多合成就是这样的特征。人们通常认为多合成是指这些语言的单词很长,但实际上,它是指将各种有意义的词组合在一起的词(来自词缀和复合词),其中单个词在欧洲语言中会翻译成整个句子。尤皮克(爱斯基摩人-阿留特家族)的插图是kaipiallrulliniuk这个单词,由kaig-piar-llru-llini-uk [be.hungry-really-past.tense-apparently-indicative-they.two]组成,意思是“他们两个显然很饿” —一个Yupik单词,整个句子翻译成英语。将名词并入动词并不是英语的有效语法特征(尽管可以在诸如保姆,后刺之类的冻结复合物中看到),但在许多美洲原住民语言(例如南提瓦语)中是常见且富有成效的(Kiowa-Tanoan家族)tiseuanmũban,由ti-seuan-mũ-ban组成[I.him-man-see-past.tense]“我看见了一个男人。”
在许多北美印第安语言中发现的其他特征包括:
-
在动词中,主题的人称和人数通常以前缀或后缀标记,例如Karukni-'áhoo'我走路',nu-'áhoo'他走路'。在某些语言中,词缀(前缀或后缀)可以同时指示其作用的主题和宾语,例如Karuk ni-mmah“我看见他”(ni-'I.him'),ná-mmah'he看见我”(ná-'he.me')。
-
在名词中,占有是用表示拥有者的人的前缀或后缀来广泛表示的。因此,卡鲁克(Karuk)拥有nani-ávaha“我的食物”,mu-ávaha“他的食物”等。(比较ávaha“食物”)。当拥有者是名词时,例如在“人的食物”中,将使用ávansamu-ávaha“人的他的食物”这样的结构。许多语言都有不可剥夺的名词,只有以这种形式存在,名词才能出现。这些不可剥夺的名词通常指亲属称谓或身体部位。例如,南加利福尼亚的一种语言Luiseño(Uto-Aztecan家族的语言)没有“我的母亲”和“您的母亲”,但是没有孤立的“母亲”字眼。
以下语法特征在北美地区较不常见,但在几个方面却与众不同:
-
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都没有拉丁和希腊语中名词变格形式的格,但是格制确实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和美国西南部的某些语言中。例如,路易莎(Luiseño)具有主格kíi:“房子”,宾格性kíiš,宾语kíi-k“到房屋”,烧蚀性kíi-ŋay“从房屋开始”,“位置性kíi-ŋa”在房屋中,工具性kíi- tal“通过房子”。
-
在许多语言中,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我们”,“我们”,“我们”的形式)在包含收件人的形式(“我们”表示“您和我”)与排他性形式“我们”之间存在区别”的意思是“我和其他人,但不是您。” 来自莫霍克族(易洛魁族)的一个例子是“我们正在写作”的全称复数tewa-hía:tons(“你们所有人,我”)与“我们正在写作”的专有复数的iakwa-hía:tons(“他们正写作”)形成对比但不是你)。某些语言在单数,双数和复数名词或代词之间在数量上也有所区别,例如,Yupik(Aleut-Eskimoan)qayaq'kayak'(一种,单数),qayak'kayaks'(两种,双数)和qayat'皮划艇”(复数,三个或更多)。重复表示全部或部分词干的重复,被广泛用于表示动词的分布或重复动作。例如,在卡鲁克(Karuk),伊玛雅“裤子”是伊玛雅“呼吸”的重复形式。在Uto-Aztecan语言中,重复也可以表示名词的复数,例如在Pima gogs“ dog”,go-gogs“ dogs”中。在许多语言中,动词词干是根据相关名词的形状或其他物理特征来区分的。因而在纳瓦霍,在参考运动,“A Ñ用于圆形物体,TA Ñ为长的物体,TI Ñ为活物,LA为绳状的物体,等等。
-
动词形式还经常通过使用前缀或后缀来指定动作的方向或位置。例如,Karuk在paθ'throw'的基础上,有动词páaθ-roov'throw upriver',páaθ-raa'throw uphill',paaθ-rípaa'throw overstream'等动词,以及多达38种其他类似形式。几种语言,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在动词上带有工具前缀,这些前缀指示了执行动作所涉及的工具。例如,Kashaya(Pomoan家族)具有这些的一些20,由根HC的形式示出ħ一个“打翻”(无前缀时,“跌倒”):BA-HC ħ A-“与鼻子打翻,” DA-HC ħ A-“与手推过去,” DU-HC ħ A-“用手指推过”,并依此类推。
-
最后,许多语言都有动词的证据形式,表明所报告信息的来源或有效性。因此,霍皮族将瓦里(他跑步,奔跑,正在奔跑)与举报事件区别开来,是瓦里克(我们)(他在田径队中奔跑)(这是对一般事实的陈述)和瓦里尼(他将要奔跑)。 ”,这是一个预期但尚未确定的事件。在其他几种语言中,动词形式始终将传闻与目击者报告区分开。
音系学
北美的语言在发音系统上与其他方式一样多样化。例如,就对比声音(音素)的数量而言,西北海岸语言区域的语言异常丰富。特林吉特有50多个音素(47个辅音和8个元音);相比之下,卡鲁克(Karuk)只有23岁。相比之下,英语大约有35位(其中约24位是辅音)。
在许多北美印第安语言中发现的辅音涉及在欧洲语言中通常找不到的几种语音对比。美洲原住民语言使用与其他语言相同的语音机制,但是许多语言也具有其他语音特征。声门停止是一种常见的辅音,声门停止是由于闭合声带而产生的呼吸中断(例如英语中的声音oh-oh!)。声门辅音在北美西部相当普遍,不是像所有英语语音一样由肺部的空气产生,而是在声门闭合和抬起时产生,因此当嘴闭合时,被困在声带上方的空气会被排出因为那个辅音被释放了。这用撇号表示;例如,它区分了Hupa(Athabaskan)的潮水“水下”和tew的“原始”。
与大多数欧洲语言相比,辅音对比的数量通常还以更多的舌头位置(发音位置)为特征。例如,许多语言将舌后部发出的两种声音区分开来–像英语中的k似的k音,再往后部产生的小舌q。唇音,同时具有唇音的声音也很常见。因此,例如,Tlingit仅具有21个后音素(中耳或小叶):中耳k,g,中耳q,G,声门状小叶和中耳k',q',唇状中耳和小耳g w,k w,k w',G w,q w,q w'以及相应的摩擦语(由嘴中某处的气流受阻而制成),例如s,z,f,v等,带有x面和面,带有小珠χ ,glottalized X 'χ'和labialized X 瓦特,χ 瓦特,X W 'χ W' 。相比之下,英语仅在这相同的一般嘴巴区域发出两种声音,k和g。
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通常具有不同类型的侧向(l形)声音(气流从舌头的侧面逸出)。除了常见的横向l(例如英语中的l)外,这些语言中的许多语言也都有清音(例如低语的l或舌头两侧吹气)。一些人有侧身,例如t和清音l一起发音,而另一些人还增加了声门的侧身。例如,纳瓦霍人共有五个彼此不同的横向声音。
在一些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对比重音是区分不同含义的词语,显著(如英语中的情况下,CON VERT与昆仑VERT)。在许多其他方面,重音固定在单词的特定音节上。例如,在图巴图巴拉(Uto-Aztecan家族)中,单词的最后音节承受重音。在其他情况下,音调(音高差异)可以区分单词,就像在中文中一样。例如,在纳瓦霍,bíní'的意思是“他的鼻孔”,“bìnì”的“他的脸”和“bìní”的“他的腰”。(高音和低音分别用尖音和重音表示。)
一些西北海岸语言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使用复杂的复辅音,如在Nuxalk(也称为贝拉库拉; Salishan家庭)TLK” w ^ IX w ^ ‘不要咽下去’。有些单词甚至完全没有元音,例如nmnmk'“ animal”。
词汇
与其他语言一样,美洲印第安人语言的单词库由简单的词干和衍生结构组成;除了复合之外,派生过程通常还包括附加(前缀,后缀)。几种语言使用内部声音替代来衍生其他词,类似于唱歌中的英语歌曲,例如Yurok pontet的“灰烬”,prncrc的“灰尘”,prncrh的“灰”。如上所述,新词汇也可以通过借阅获得。
应该注意的是,一般而言,在语言中,词汇项的含义不一定必须从其历史渊源或部分含义来推断。例如,一个19世纪早期的捕兽人麦凯(McKay)的名字以“ karkay”的名字进入了Karuk,但含义为“白人”。当它与本地名词váas“鹿皮毯”复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一个新词,从而赋予了新词“makáy-vaas”“布”,又与yukúkku“莫卡辛”复合而成了makayvas-yukúkku“网球鞋”。在词汇形成的每个阶段,意义不仅取决于词源,还取决于语义值的任意扩展或限制。
词汇在它们指定的事物的数量和类型方面有所不同。一种语言可能会在特定的语义领域做出许多特定的区分,而另一种语言可能只会有一些通用术语。差异与语义区域对特定社会的重要性相关。因此,英语在牛类动物(公牛,牛,小牛,小母牛,牛,牛,牛)的词汇中非常具体,甚至缺少单数形式的通用称谓(什么是牛的单数形式?),对于其他物种,它仅具有一般保护条款。例如,在借用鲑鱼种类的名称之前,英语只有鲑鱼的统称,而某些萨利山语言对6种不同种类的鲑鱼有不同的称呼。可以预期,北美印第安人的词汇体现了反映美国本土环境条件和文化传统的语义分类。西北太平洋地区语言中与鲑鱼相关的术语数量反映了这些文化中鲑鱼的显着性。简而言之,在某些语义领域中,英语可能比某些美洲原住民语言做出更多区分,而在另一些语义领域中,则比在那些语言中做出更少的区分。因此,英语将“飞机”,“飞行员”和“飞虫”区分开来,而霍皮语则将单个,更通用的术语称为“飞行者”,大致上是“飞行者”,而英语则将单个术语统称为“水”,而霍皮语则将其区别开pauhu是自然界中的水,来自kuuyi“水(含水)”,没有一个“水”术语。
语言文化
从词汇,语法和语义上表现出来的美洲印第安人语言看似异国情调的特征,已导致学者们推测语言,文化和思想或“世界观”(对世界的认知取向)之间的关系。据推测,每种语言都体现着一个独特的宇宙组织,它支配着个人的感知和思想习惯,从而决定了相关的非语言文化的各个方面。正如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在1929年所说的那样,
人类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
。
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已成为其社会表达媒介的特定语言。
。
事实是,“现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建立在该群体的语言习惯上的。
。
我们看到,听到和体验到的其他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一样,因为我们社区的语言习惯会导致某些选择的解释。
Sapir的学生Benjamin Lee Whorf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与美洲印第安人语言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想法,现在通常被称为Whorfian(或Sapir-Whorf)假设。Whorf的最初论点着眼于英语和美洲原住民说“同一件事”的方式之间的显着差异。从这种语言差异中,Whorf推断出思维习惯的根本差异,并试图证明这些思维方式在非语言文化行为中的体现。r夫在他的流行著作中声称语言决定思想。他最著名的例子涉及霍皮族的时间处理。Whorf声称,霍皮人比物理学上比SAE(欧洲标准平均语言)更适合物理学,他说霍皮人以事件和过程为中心,以事物和关系为英语。也就是说,霍皮文语法强调时态(执行动作时)的方面(如何执行动作)。众所周知,Whorfian假设很难进行测试,因为设计实验很难将语言造成的后果与思想造成的后果区分开。但是,美洲印第安人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继续为其调查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实验室。
一个流行但非常扭曲的说法是,在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中有很多“雪”的词。这被称为“伟大的爱斯基摩语词汇骗局”。这种说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断增加“爱斯基摩人”中不同的“雪”字的数量,有时甚至声称成百上千。有人以某种方式说明了世界根本不同观点的沃尔夫论点,有时这种观点与影响语言的环境决定论有关。事实是,只有一种爱斯基摩语的字典声称“雪”只有三个词根。对于另一种爱斯基摩人的语言,语言学家大约有十二名。但是,即使是基本的英语,也有很多“雪”词:雪,暴风雪,雨夹雪,乱舞,漂流,雪泥,粉末,薄片等。
误解始于1911年,来自美国人类学和美国语言学创始人Franz Boas的例子,他的目标是警告不要进行肤浅的语言比较。作为肤浅的跨语言差异的一个例子,博阿斯列举了四个因纽特人的积雪根源-称“地面上的雪”,“加纳”“落雪”,“ piqsirpoq”“飘雪”和qimusqsuq“有雪漂流”,并将其与英吉利河进行了比较。 ,湖泊,雨水和溪流,其中对不同形式的“水”使用不同的词,类似于因纽特人对不同形式的“雪”使用不同的词。他的观点是,因纽特人(inuit)有着不同的“雪”根源,就像英语一样,有着不同的“水”根源,这是语言变化的肤浅事实。他对因纽特人中“雪”这个词的数量一无所知,对语言与文化或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确定性关系一无所知。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北美史前学生所感兴趣的,即,语言保留了文化历史变迁的痕迹,因此有助于重建过去。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讨论了确定原始家园的位置的技术,该语言家庭的相关语言从这些祖国中散布。其一是在语言多样性最大的地区更容易找到家园。例如,不列颠群岛的英语方言与最近定居的地区(如北美)的方言差异更大。以美洲印第安人为例,阿萨巴斯坎语言现已在西南地区(纳瓦霍,阿帕奇),太平洋海岸(托洛瓦,休帕)和西亚北极地区发现。亚北极语言之间更大的多样性导致了这样一个假说,即阿萨巴斯坎语言散布的原始中心就是那个区域。1936年,萨皮尔(Sapir)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阿萨巴斯坎人的北部起源。他在萨普尔重建了史前阿萨巴斯坎语词汇的部分内容,例如,“牛角”一词如何成为“汤匙”作为祖先的意思。纳瓦霍人从遥远的北方(在那里他们制作了鹿角的勺子)迁移到了西南地区(在那里他们从葫芦中制成了勺子,而北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语言发现与考古学数据的关联为美洲印第安人史前研究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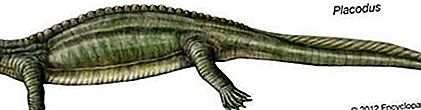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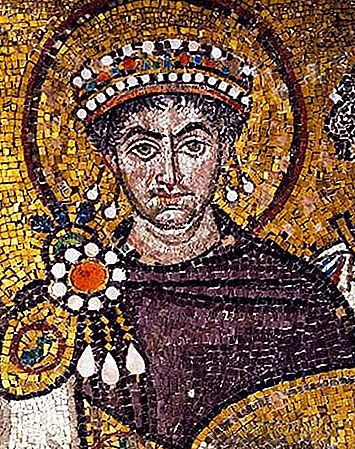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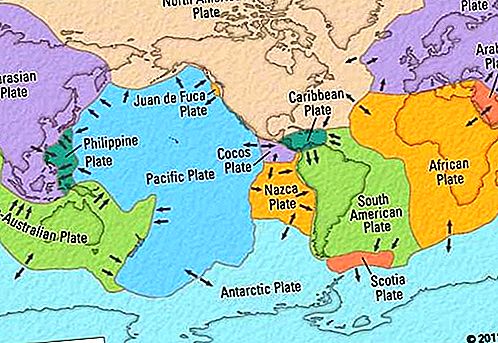
![美国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2009] 美国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2009]](https://images.thetopknowledge.com/img/politics-law-government/7/american-recovery-reinvestment-act-united-states-2009.jpg)




